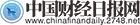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太空活动通常指人类在距离地表100公里以上空间开展的活动。时空基准是人类测定和描述宇宙中事物时间和空间坐标的统一参考基准,包含了由真实天体和人造物体组成的参考框架和基准物体与基于人类协调统一定义的多层次时空参考系。
由于星空中的遥远天体恒久存在且运动规律精准可循,古往今来,时空基准的源头均来自宇宙中的天体。其中,民用时间源自地球相对遥远天体的自转、空间方向基准源自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轴相对遥远天体的方向,方向恒定不变的河外类星体也是良好的惯性基准。得益于天文学、物理学和测量学的发展,作为时空基准源头的各类天体逐步被人类观测并信息化。天文学家一般将运动学方式记录方向变化缓慢的恒星和类星体等天体的位置、运动等信息表册称为星表;将以动力学方式记录方向变化快速的太阳系天体的轨道数据表册称为历表;将记录脉冲星脉冲周期特征与脉冲星位置和运动等信息表册称为脉冲星星历表。
宇宙中包括多种类型的天体,发射着各种波段电磁辐射,相关测量在不同局域间给予技术实现。为了更好开展太空活动,需要有完善技术保证且系统统一的时空基准,多波段测量基准的统一是局域到全域深空飞行器定姿、定位和定轨的基础。无论距离地球多远,基础性工作就是掌握星表历表等时空基准源头数据(图1)。
 (资料图)
(资料图)
太空活动时空基准涉及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深度融合,其技术构建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对于大国战略安全、航天技术发展、深空探测水平和基础物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技术现状,对比分析了我国当前差距和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太空活动的时间基准系统
太空活动多由飞行器承载,1 ms时间误差对应的飞行器位置偏差可达7m,故飞行器测控角度需时间统一[1]。这其中,地面原子钟、星载原子钟技术、紧密关联地球自转的世界时一类修正(universal time 1,UT1)实时测量技术、时间频率同步与传递技术是支撑太空活动时间基准系统的核心技术。
基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形成的国际规范,地球以外乃至整个太阳系内的任何太空活动对于时间测量的定义、变换规则、工程实现方法与地面处理方式一致,现有相对论时空度规理论已较好地支撑了人类一系列宇航深空探索活动[2]。需指出,按照广义相对论,时空不可分割且测量具有局域性、并对所有观测者都是“平权的”,对国际标准单位制的“SI秒”和“SI米”的直接测量并不限定地点或引力场。为了系统统一,需配套大范围适用的变换规则,这是创建和使用时空基准的基本任务之一,并属于基本天文学研究范畴。
太空活动的空间基准系统
空间是描述事件和物体的距离、方向坐标分量,空间基准系统是测定天地间所有物体和事件的距离、方向、姿态及其变化的参考系统,具体由国际天球参考架(international celestial reference frame,ICRF)、国际地球参考架(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ITRF)和地球定向参数(earth orientation parameters,EOP)等实体和参数实现。
由于地球整体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其空间姿态体现为时变的三维转动,这个称为EOP,它描述了国际地球参考系(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system,ITRS)相对地心天球参考系(geocentric celestial reference system,GCRS)的运动姿态变化。EOP包括5个参数:描述地球自转轴在惯性空间指向变化的2个岁差章动角;描述地球自转轴相对于地球表面变化的2个极移角;描述地球绕自转轴转动的1个自转角,即此角也用于计算UT1。这些参数构成了卫星轨道实时测算的重要依据。
在IAU、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等国际联合会共同领导的国际地球自转与参考系服务机构(IERS)协调下,在各个参与国家提供观测设施、参与数据处理分析、合作科学研究等多种形式合作下,基于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卫星激光测距(SLR)、卫星多普勒定轨定位(DORIS)、各类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以及多种类多波段的天文望远镜测量等系统,已创建了多套可免费获取的全球统一ITRF、ICRF和EOP产品。目前最新的ITRF2014还考虑了地壳的非线性运动和地震的影响,精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经典大地测量时代,大地基准以经纬度及高程表示,体现为国家、地区的区域特性。卫星导航技术出现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需与地面基准控制点和坐标取得协调。例如,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的WGS84坐标系统是1984年定义的国际协议,这是为GPS使用而建立的全球地面坐标系统,相当于某一时间点上的国际地面坐标标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的BDCS坐标系统,则与中国测绘部门发布的大地坐标系CGCS2000一致。这类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经典大地测量的区域性基准不同,需与ITRF连接进而实现全球统一。目前,美国最新的WGS84连接到了国际ITRF2008,而我国BDCS是连接到了ITRF2000。
国内外太空活动时空基准发展现状
原子钟和UT1是把控时空系统的核心技术
目前,卫星导航系统的时空基准均建立在地面,各卫星导航系统依靠全球或区域监测站的观测数据测定卫星轨道和星上钟差,并通过卫星播发广播星历和钟差实现高精度时空基准的传递。所有导航卫星均配置了星载原子钟,主要包括铷原子钟、铯原子钟和被动型氢钟。美国海军天文台在原子时自主守时方面发挥了国际引领和主导作用。美国国家时间频率准确度已达到10-15,时间同步精度达到纳秒量级,在国际原子时产生中拥有最大权重。美国GPSIII卫星配置的增强型铷原子钟日稳定度达到10-15量级。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守时和授时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由于缺乏10-16稳定度守时钟技术,与美国存在性能上的差距。但BDS建设加速推动了技术进步,北斗三号卫星配置的铷原子钟日稳定度达到了10-14量级,正加速追赶国际一流水平,被动型氢原子钟日稳定度达到10-15量级,和欧洲伽利略星载氢钟指标相当。
UT1表征了地球的真实自转角度,一切联系地面和空间目标测量信息均需要这个量,使得其在国家标准时间产生、深空探测、卫星导航等领域有重要应用,其中多数情况需要实时或准实时UT1。例如,在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致使居家办公,美国GPS、俄罗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LONASS)和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Galileo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曾联名支持UT1的准实时国际联测,以保持导航卫星系统的服务精度。光学照相测量技术也曾在UTI测量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精度相比于现今最精确的VLBI有量级差异。
目前,国际上UT1数据产品的权威发布机构为IERS,测量UT1等参数需要全球VLBI观测站网。为此,美国航天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GSFC)牵头成立了国际测地与天体测量VLBI服务(IVS)机构,从而协调全球VLBI站网参加UT1的观测、相关处理、数据分析,为IERS提供数据源。上海天文台是IVS的正式成员和数据分析中心之一,自1987年开始参加国际联测,目前每年参加约30次,不定期向IVS提供射电ICRF、ITRF和EOP等解算结果。在上海天文台的支持下,国家授时中心和我国深空网均开展过UT1观测实验,有关单位合作初步构建了可代替互联网UT1下载服务的能力,但由于刚起步,还未形成UT1服务的全产业链。
目前我国UT1参数取自IERS,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则一直保持独立测定工作。但近年国际形势突变,完全依赖国外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此,我国也积极部署,有望在近2年实现全套EOP参数独立测量和自主产品服务能力,但在基础科研、人才队伍扶持等方面还有不足。
星表和历表研制技术
国外星表与历表发展
国外有记载的最早星表是希腊人阿里斯提鲁斯等于公元前260年所著的星表,包括近几百颗星且位置精度都在1度水平。人类最早的星表是公元前360年我国石申等人编制的《石氏星经》,比国外早了近100年。但随后欧洲科技发展提速,17世纪发明天文望远镜、19世纪发明天文照相术,积累了大量地面观测数据。1988年,德国编制了亚角秒级FK5星表,在位置精度、恒星数目方面有了巨大提高,是当时国际最高精度的基准星表。1991年IAU决议采用银河系外的类星体作为国际天球参考系的基准源,1997年欧洲航天局(ESA)第1颗天体测量卫星任务带来了依巴谷星表,随后开启了空间天体测量的时代。依巴谷星表是国际天球参考系更新定义后的首次光学实现[9]。同一时期,天文学家在地面启用了VLBI,基于近30年国际联合观测累积,截至目前已实现了射电天球参考架的4次升级,在数量、位置精度和频段覆盖宽度等方面均有很大提高。2013年ESA发射了盖亚(Gaia)卫星,致力于持续积累观测和处理数据,并分期发布星表产品。目前,Gaia任务成果发布的星数已达20多亿,最终天体测量精度将达到5—10微角秒水平,这将会成为人类至今创建的最高精度和最高密度的ICRF。此外,国外还编制出了多个基于地面照相观测的星表和针对其他特殊目的星表,如暗星星表、变星星表、黄道星表、导星星表、特殊红外波段星表等。
太阳系天体历表在飞行器定轨、深空探索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赖于地基天文观测和深空探测数据的长期积累,太阳系天体历表精度逐步提升。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自20世纪60年代开创了高精度数值历表研究;70年代初,其发布的DE系列历表成为世界标准。DE系列先后根据不同目的发表了多个版本,在天体数量、参数精度、时间跨度等方面不断升级,当前最新版本为DE440/LE436。俄罗斯科学院应用天文研究所(IAA)从1974年开始独立研制出了EPM系列历表。法国历书编算与天体力学研究所(IMCCE)从2003年起开始研制INPOP系列历表,目前指标已达到美国DE系列历表水平。目前国际上仅有美、俄、法3个国家具有公开发表高精度数值历表的实力,并且实力还在不断提升。
我国星表与历表发展
由于欧美星表和历表产品基本可满足我国军民领域的相关需要,故我国一直采取了国际合作的策略,对欧美星表和历表产品以采用为主,贡献有限。近几年来,依托国内射电望远镜,上海天文台开展了黄道带天区的射电星表加密工作,并基于数字化施密特照相巡天数据,编制出我国第1部绝对自行星表(absolute proper motions outside the plane,APOP)。紫金山天文台1984年起开始基于美国DE历表编算天文年历,并于2005年形成了PMOE2003(purple mountain observatory ephemeris 2003)历表,但框架初值、物理和天文常数取自DE405,未能实现完全独立自主。
尽管我国目前缺乏国际权威产品,但在围绕星表和历表建立所需的天体力学、天体测量和行星科学方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基础,掌握了微角秒级星表的相对论模型创建和软件开发技术,星表和历表研究评估的技术储备扎实,潜力巨大。随着深空探测任务的增多,合理利用我国构建的深空测控网[13],也能提升构建星表和历表的能力。
脉冲星计时观测技术
根据过去30年对脉冲星的不断观测,目前已知脉冲星的长期稳定度最高可达10-15,这距离当今最高精度原子钟的稳定度还有一定差距,但自从1982年第1颗毫秒脉冲星PSR B1937+21被发现以来,在自然界探寻最高稳定度的脉冲星已成为天文学家的梦想,这也是太阳系及其外更大范围深空乃至星际探索所需的潜在时空基准源之一。近期,ESA已开展了脉冲星时间标准方面的研究,即PulChron计划,并部分实现了可溯源的脉冲星时间标准。国际上也逐渐形成了若干脉冲星计时阵合作组织,并联合构成了国际脉冲星测时阵(international pulsar timing array,IPTA)。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单位长期开展脉冲星计时观测,在脉冲星钟频率稳定度估计、综合脉冲星时算法等方面积累了研究基础和人才队伍。但前期受限于设施测量能力水平,直到2016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建成后,才实现了对少数脉冲星百纳秒的测时精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FAST在脉冲星观测方面仍存在观测时间不足、天区覆盖有限、观测频率无法拓展到3GHz以上等短板。由此可见,我国脉冲星观测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其他专用精密时空框架
自1969年以来,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成功发展了基于人造信标的太空活动时空基准技术,包括月面和火星表面激光角反射器、地月之间主动激光测量、地火之间多普勒测量技术,并且在火星周围运行多个中继卫星。目前,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基于人造信标的太空活动时空基准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把飞抵火星原有50%的失败概率几乎降低到了零。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均提出在地月空间通过探测器发播人工脉冲实现深空基准星座的技术,现国外已出版了相关技术的白皮书,而我国在个别方向上处于论证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嫦娥四号中继卫星仅承担对月球着陆器的接力通信工作,不具备微波接力测量或构建基准的能力,且我国还没在月面部署激光反射器。
当前我国太空活动时空基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在个别方面有相当好的水平,但作为航天大国,我国太空活动时空基准的整体层面存在基础设施水平不高、科研根基不实、不具备系统性产品服务能力、对国外依存度大的问题。
目前,我国星表、历表、地球自转参数等数据主要来自国外组织机构的互联网平台,这不具有长远性和可靠性。例如,在我国某些航天任务关键时刻,曾多次发生IERS临时维护而暂时停止其EOP服务的事件;我国小天体探测任务目标2016HO3小行星和311P彗星在国内无实测数据,所以只能分析国外数据,且缺乏观测验证能力;我国有些太空遥感任务所需的红外星表国外未共享,只能依靠光谱模型理论推算;北斗二号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没及时更新太阳系天体历表,导致无法精确计算太阳和月亮对卫星的引力摄动,曾导致轨道计算和预报业务暂时中断。
长此以往,我国在卫星导航、近地小行星探测、空间安全、大地测绘等将逐步陷入基础时空定位信息精度不断下降以及难以校核的困境。
当前问题的主要原因
安全性战略性认识不够。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时空基准源头建设重视不够,忽略了其在卫星导航、深空探测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战略意义。我国太空活动起步于火箭卫星等国防应用急需,起初精度要求也不高,尚未系统布局时空基准的设施建设,对于星表、历表和EOP的作用价值也认识有限。其次,“拿来主义”思想使得我国科研人员形成了依赖国外产品的惯性,没有深刻意识到星表、历表等参数自主可控的重要性。
历史积累和研发投入不足。星表和历表研制是极其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精密先进的天基和地基观测装置,更需要长期的观测积累。欧美国家在前人肩膀上持续更新提升,具有长期稳定的队伍,沉浸于细致入微的理论和数据分析。我国对太空活动时空基准的源头星历表从未进行系统性计划支持,投入不足,人才队伍不稳定,设施发展迟缓。
系统性科研与重大任务牵引缺失。我国相关单位在星表改进、天文年历编算、太阳系小天体研究等方面,多是应零散性、临时性、紧急性任务的要求而开展,科研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意识不强,满足于应付眼前和一事一议,缺乏试用试错再改进的机会,产品化能力和系统性积累不足,导致大量技术成果长期走不出实验室。我国虽然在某些方向的研究水平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没有形成面向各类航天任务统一的时空基准权威性框架产品,更没有实现从科学研究到服务能力的持续转化。
在航天用户部门方面,我国倾向于重大工程构建,并不关注其基础性源头性建设问题。然而,美国JPL的DE系列历表很多更新就是为了具体深空探测任务所经历引力场环境不同而研制的;法国INPOP系列历表的发展则主要源自于ESA的Gaia天体测量任务和其观测资料的微角秒级处理分析需求。由此可见,我国在太空活动相关时空基准方面的系统性科研与重大任务牵引上还缺乏基础科研建设,并存在部分思想认识问题。
发展思路建议
我国正在从航天大国转向强国的路上,空间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从地球空间向地月空间、月球空间、太阳系行星际延伸,而诸如北斗工程、嫦娥工程、火星探测和小行星探测等重大航天工程任务,都要求掌握高精度时空基准源头数据。“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面向空间重大活动需求,务必提高认识,强化任务工程化、工作持久化、能力系统化、成果服务化和研究国际化的思维与理念,以尽早为我国太空活动提供自主可控且国际先进的各类时空基准服务。建议发展对策如下:
加强基础研究。建议在国家层面对太空活动时空基准的基础研究给予稳定支持,主要包括:加强新型高精度原子频率标准相关的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等前沿科学研究,并加强基础材料工艺攻关;开展相对论框架下的照相天体测量模型研究、数据处理方法研究等工作,为独立创建红外星表奠定基础;深入开展相对论时空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引力场参数测定研究,深化太阳系天体动力学建模研究;深入开展脉冲星计时和定位探测技术,解析低频噪声来源,建立脉冲星历表,这是任何利用脉冲星构建时空基准系统所无法绕开的基础工作。
加强顶层设计。要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与协调论证。太空活动时空基准的构建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技术的战略性系统工程,不能全靠零散科研,必须从国家顶层上加强对应用需求、任务目标、技术方案的设计和论证,建立国家级的专业人才队伍,研究促进航天任务和天文科研有机协同机制。
加强资源统筹。调研既有技术条件,集约化利用已有存量,理清体系关系,统筹相关规划。统筹不同渠道安排的观天测地设施,从而高性价比地实现对太阳系行星和基本物理参数进行自主高精度测量。例如,应用上协调好设施能力、地理位置、时段分配和联测需求,合理规划调配;深入开发我国探月工程、深空探测计划的产出潜能;在每次任务中增加行星观测实验,设置合作探测目标。
加强观测能力。加快补齐观测设施短板,增补构建若干地基和天基专用系统。例如,为高精度自主化提供UT1实测数据并兼顾精化ICRF,应研究布局天地一体的VLBI联测系统;针对脉冲星开展以FAST为核心,并适当增补中小型射电装置阵列的能力建设。这不仅能补足脉冲星观测短板,还能通过VLBI组网实现脉冲星星历表与射电星表的连接和加密,也将为人类开展深空甚至星际探索提供潜在的时空基准源。
加强国际合作。在EOP和UT1产品服务能力方面,贡献我国近些年部署的观测设施和数据,争取牵头组织空间基准方面的国际联测活动,带动服务能力提升;在射电星表方面,继续加强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空间大地测量方面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联测和数据处理,加速提高自主创建射电星表的能力;在光学星表方面,继续深化与ESA的Gaia项目合作,在相对论模型创建、观测图像微角秒级数据处理、星表独立评估等方面深度参与;在太阳系历表方面,加强同美、俄、法的合作交流,积极牵头组织国际计划,增强国际话语权。我国曾作为核心参与IAU关于太阳系时间系统转换理论创建和规范制定工作,在基本天文学领域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继续坚持国际化视野和胸怀,持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作者:肖伟刚,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齐朝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广告
X 关闭
- 【天天新视野】乡村卫生室每天下班都在门上贴满退烧药: “免费拿 不要钱” 2023-01-29
- 每日快播:【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优化政策供给 强化系统集成 2023-01-29
- 实时:2022福建永定土楼马拉松赛鸣枪开赛 2023-01-29
- 日媒:在日本出生的大熊猫“香香”将于明年2月归还中国 2023-01-29
- 【速看料】第十五届闽台陈靖姑民俗文化旅游节在福州开幕 2023-01-29
- 广西文物摄影师十余载弯腰“定格”历史 让文物“活”起来 2023-01-29
- 中石油加工能力最大的延迟焦化装置在广东揭阳实现投料 2023-01-29
- 今日热议: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发布,山东160家入选,居全国首位! 2023-01-29
- 一座中原煤城与红嘴鸥的“双向奔赴” 2023-01-29
- 【世界时快讯】西安地铁6号线二期已具初期运营条件 站内“景观”续写“古今长安” 2023-01-29
- 环球新动态:建设银行召开“向往的力量──中国建设银行‘双子星’App发布会”
- 全球观天下!中国唯一盐湖勘查专业队:揭开“聚宝盆”丰富矿产资源“面纱”
- 当前信息:宁吉喆:中国经济恢复性增长将减缓全球经济衰退程度
- 天天百事通!兵装集团中国长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开工
- 姆巴佩对阵摩纳哥进球后没有选择庆祝,那里是他成长的地方
- 每日热议!上海为快递员、外卖小哥阶段性发放稳岗补贴
- 关注:我们的好朋友⑫|“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放歌鹊山水库,一鸣惊人成生态“宣传大使”
- 每日观点:功勋主帅!斯卡洛尼家乡的街道将以他的名字命名来表彰他
- 全球今亮点!村里的骄傲!大马丁携金手套奖回到家乡,10万人到场前来祝贺
- 官方:广州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恒大足校校长王亚军被开除
广告
X 关闭
- 1 世界速看:巡查供暖线路、提供精准服务,各地多措并举—— 服务暖融融 百姓好过冬(确保群众温暖安全过冬①)
- 2 【环球快播报】用优质电影供给提升农村文化质量
- 3 办好办实群众身边事(身边事·年终特别报道)
- 4 跨越两千公里的“援”梦之旅
- 5 当前速递!这份“全球美食排行榜”被疯狂吐槽,竟把台湾当做“国家”纳入排行
- 6 今日讯!又有39人终生禁驾!交通违法次数较多的“两客一危一货”车辆、运输企业也被曝光
- 7 全球快报:乌方称俄一停有战略轰炸机的军用机场传出爆炸声,俄官员称正核实
- 8 时讯:2022年中国棉花实现增产
- 9 快资讯丨中央气象台:弱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方 南方将有雨雪天气
- 10 全球热讯:掌握争冠主动权!山东泰山因梅州弃权躺拿3分,暂登顶中超榜首